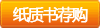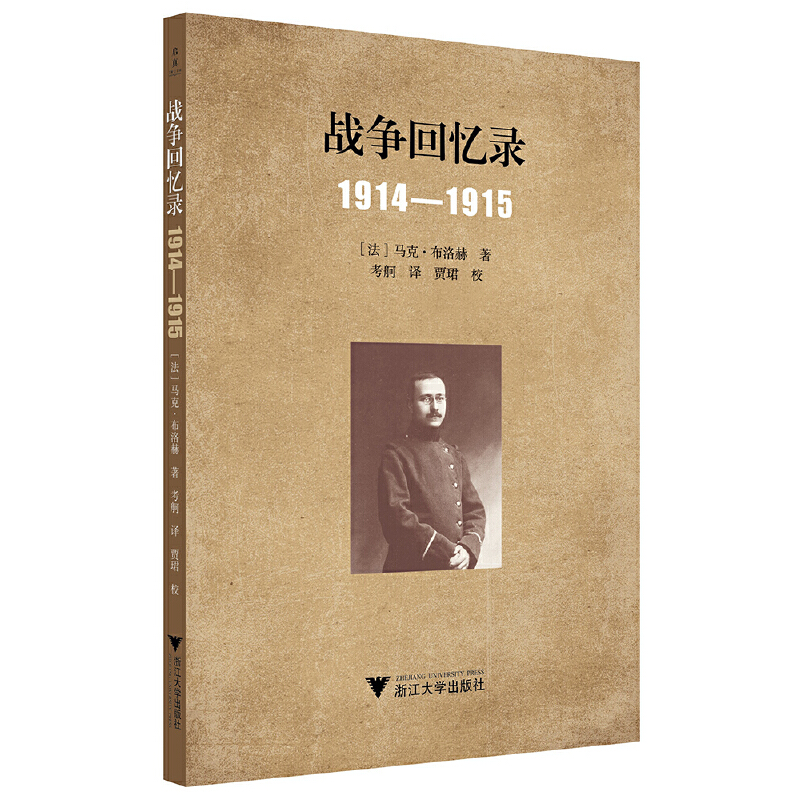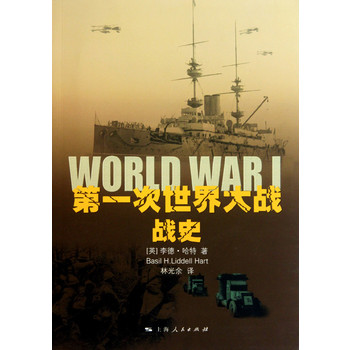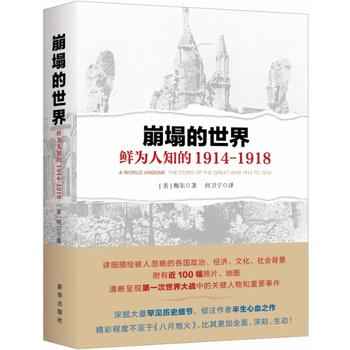ΓΓΓΓ
Ψéί΄ΆΤΥ]1ΘΚΓΑάμΫβ“Μëπ(zh®Λn)���Θ§“Μ±ΨïχΉψ“”����Γ���ΘΓ±
2014Ρξ”Δ΅χΙΰ»ϊ†•-Χᆕ¬ϋΣ³ΡξΕ»ΉςΤΖ�����Θ§÷v ω“Μëπ(zh®Λn)ΚσΒΡΟώ÷ς�ΓΔΒέ΅χ��ΓΔάδëπ(zh®Λn)�����ΓΔΟώΉε÷ςΝx�����ΓΔΌY±Ψ÷ςΝx���ΓΔΥ΅–gΚΆ‘äΗηΓΘ
Ψéί΄ΆΤΥ]2ΘΚΈ÷†•Ζρ…≠öv ΖΣ³ΒΟ÷ς¥σ–l(w®®i)·άΉ÷ZΤùÉAΝΠ÷°Ής�����Θ§BBC“Μëπ(zh®Λn)ΑΌΡξΦoδ¦Τ§ΓΕιLιLΒΡξé”ΑΓΖΡ_±Ψ‘≠÷χΘ§Ής’Ώ”H»ΈΫβ’f�����ΓΘ
”Δ΅χ¨W–g‘Κ‘Κ Ω���ΓΔ³Π‰ρ¥σ¨Wöv Ζ¨WΫΧ Ύ�ΓΔ”Δ΅χ Ζ¨WΫγΙε¨ö¥σ–l(w®®i)·άΉ÷ZΤù¥ζ±μΉςΤΖ�Θ§BBC“‘ΓΕιLιLΒΡξé”ΑΓΖûιΡ_±ΨΘ§÷ΤΉςΝΥ»ΐΦ·Ά§ΟϊΦoδ¦Τ§�����Θ§≤Δ―ϊ’àάΉ÷ZΤùΫΧ Ύ‘ΎΤ§÷–™ζ»ΈΫβ’f�����Θ§ΉΖ¨ΛΒΎ“Μ¥Έ άΫγ¥σëπ(zh®Λn)‘ΎΤδΫY χ÷°ΚσΒΡ100ΡξιgΦΑ10²Ä≤ΜΆ§΅χΦ“ΒΡΏz°a���Θ§≤Δ«“ôzΥς¥Υ¥Έëπ(zh®Λn)†é «»γΚΈΉ¨“Μ¥ζ»ΥΕΦσ@ΜξΈ¥…Δ≤ΔΥή‘λΝΥëπ(zh®Λn)ΚσΒΡΚΆΤΫΡξ¥ζ����ΓΘ
Ψéί΄ΆΤΥ]3ΘΚ»Ϊ«ρ20Φ“÷ΊΝΩΦâàσΩ·κs÷ΨΧΊ³eΆΤΥ]ΉxΈο
ΓΕΫπ»ΎïràσΓΖΓΕ»A ΔνDύ]àσΓΖΓΕΧ©Έν ΩàσΓΖΓΕ≤® ΩνD≠h(hu®Δn)«ρàσΓΖΓΕ»A†•Ϋ÷»’àσΓΖΓΕΣöΝΔàσΓΖΓΕ–¬¬³÷ήΩ·ΓΖΓΕΈΡ¨W‘u’™ΓΖΓ≠Γ≠
ΓΓΓΓ
ΓΓΓΓ
ΗϋΕύΨΪ≤ ΚΟïχΘΚ
ΓΓΓΓ
ΓΓΓΓ
‘Ύ”Δ΅χ��Θ§“Μëπ(zh®Λn)“―Ϋ¦±Μ»Υ²ÉΏzΆϋΕύΡξΝΥ����ΓΘηb”Ύ±äΕύΒΡ–Γ’fΦ“Θ§÷T»γ≈…ΧΊ·ΑΆΩΥ�����ΓΔ»ϊΑΆΥΙΒΌΑ≤·Η���ΘΩΥΥΙ“‘ΦΑΒΊΈΜο@Κ’ΒΡΆΰ†•ΗΞάΉΒ¬·öWΈΡΚΆΤδΥϊ“Μëπ(zh®Λn)‘ä»ΥΒΡΉςΤΖ…ν ήΟώ±äög”≠�Θ§…θ÷Ν±ΜΝ_Ν–‘Ύ¨W–ΘΒΡ’n≥Χ±μάοΟφ�Θ§≥…ûι¨W…ζΒΡ±ΊΉxïχΡΩΘ§Ώ@–©ÉAœρΩ¥Τπ¹μΥΤΚθΖ«≥ΘΤφΙ÷��ΓΘ»ΜΕχ����Θ§1914-1918ΡξΏ@“ΜΕΈöv ΖΥΤΚθ“―Ϋ¦≥…ûιΈΡ¨WΦ“ΙPœ¬ΒΡëπ(zh®Λn)†é�����Θ§“ρΕχΟ™κxΝΥΥϋΒΡöv ΖΜυΒA≈cÉ»Κ≠ΓΘ’ΐ»γöWΈΡΥυ’f����Θ§ΓΑΈ“ΒΡ³™(chu®Λng)Ής÷ςν} «ëπ(zh®Λn)†é“‘ΦΑ¨Π”Ύëπ(zh®Λn)†éΒΡΏzΚΕΓ±Θ§ΓΑ¨Π“Μëπ(zh®Λn)ΒΡ’™ ω÷ς“Σ «Μυ”Ύ‘äΗη«ιë―Γ±Γ��Θ§F‘ΎΈ“²É¨Π”ΎΗΞΧmΒ¬ΥΙΚΆΤΛΩ®ΒΎ’”ù…ΒΊÖ^(q®±)―ΣΝς≥…Κ”ΒΡëπ(zh®Λn)†éàωΟφΒΡΟη¨ëΏ^”ΎΟτΗ–��Θ§’JûιΥϋ²ÉΚΝüo“βΝx����Θ§’JûιΏ@ «“Μàω±·³ΓΓΣΓΣΡ«–©οL»A’ΐΟ·ΒΡΡξίp»Υ≤Μ÷ΣΒάΥϊ²É?y®≠u)ι÷°ΗΕ≥ω…ζΟϋΒΡΏ@àωëπ(zh®Λn)†éΒΡ“βΝxΚΈ‘ΎΓΘΒΪ «, »γΙϊΑ―Ώ@àω¦_ΆΜÉHÉHΫΒΒΆΒΫ²Ä»Υ±·³ΓΒΡ¨”Οφ�����Θ§≤ΜΙή‘θΟ¥Η–³”»Υ��Θ§Έ“²ÉΨΆ ß»ΞΝΥ¨Πöv Ζ¥σ±≥ΨΑΒΡΗ–÷ΣΡήΝΠ�����Θ§Εχ¨Π”Ύ“Μëπ(zh®Λn)ΒΡ’™ ω“―Ϋ¦≥ΝΟ‘”Ύ¨Π‘äΗηΒΡ«ιë―Εχ’Ιι_�ΓΘ
‘Ύ¨W–g Ζ…œ��Θ§èΡöv Ζ¨”ΟφΒΡ’™ ωόDœρΈΡΜ·¨”ΟφΒΡΖ÷ΈωΏ@ΖNΎÖœρ≤Μîύ±ΜΧα…ΐ�ΓΘ“‘1914-1918ΡξΒΡ“Μëπ(zh®Λn)ûιάΐ����Θ§Ώ@ΖNΎÖœρ“―¨ß÷¬»Υ²É¨Π”Ύ“Μëπ(zh®Λn)ΒΡΙΪΙ≤”¦ë¦Ώ^”ΎΟ‘ëΌΘ§Ώ@ΖN”¦ë¦≤Μ «Μυ”Ύ ¬¨ç���Θ§Εχ «Μυ”Ύ«ιΗ––‘ΒΡΫβΉx���ΓΘΉ‘20 άΦo80Ρξ¥ζ“‘¹μΘ§±äΕύΒΡ¨W’Ώ“―Ϋ¦ΫβΉxΝΥ“Μëπ(zh®Λn)ΒΡΈΡΜ·”Αμë���Θ§ΧΊ³e «¨Π”ΎΥάΆωΒΡ»ΥΦΡΆ–ΑßΥΦΒΡ«ιΗ–�Θ§ΕχΏ@–©¥_¨ç «±Μ²ςΫy(t®·ng)ΒΡήä ¬ Ζ¨WΦ“ΥυΚω“ïΒΡÉ»»ί���ΓΘΒΪ «, ΧΪΏ^”Ύœύ–≈Ώ@ΖN”¦ë¦���Θ§ΨΆœώ§F‘ΎΒΡ Ζ¨WΨéΉκΎÖ³ί“Μ‰”Θ§κxι_÷ςν}ΧΪΏh�Θ§ÖsΆυΆυΚω“ïΝΥëπ(zh®Λn)†éΒΡ’ΰ÷ΈΓΔήä ¬�����ΓΔΫ¦ùζ��ΓΔ…γïΰΚΆ÷ΣΉRΒ»÷±Ϋ”ΒΡΚΆΈοΌ|¨”ΟφΒΡ”Αμë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ΘΓΕιLιLΒΡξé”ΑΓΖΏ@±Ψïχ�����Θ§ «“Μ±ΨΦ»ξPΉΔ ≈’Ώ”÷ξPΉΔ§F¨çΒΡïχ��Θ§“ρûι1918Ρξ“‘ΚσΒΡ…ζΜν»‘‘Ύά^άm(x®¥)�����ΓΘ ¬¨ç…œ�Θ§’ΐ»γΈιΒ¬Ν_·Άΰ†•ΏdΒΡ Ήœ·Αl(f®Γ)―‘»ΥÜΧ÷Έ·ΗώάΉ†•‘Ύ1920ΡξΥυ÷Η≥ωΒΡΡ«‰”�Θ§Ώ@ «“Μ²Ä±Μëπ(zh®Λn)†éΒΡΜπ―φ÷ΊΥήΒΡïr¥ζΓΘ ¬¨ç…œ����Θ§ëπ(zh®Λn)ΚσöW÷όΒΡ¥σ≤ΩΖ÷΅χΦ“≤Δ¦]”–œί»κ”άΚψΒΡΑßΥΦ÷°÷–�Θ§20 άΦoΒΡΕΰ»ΐ °Ρξ¥ζ“≤≤Δ≤Μ «“Μ²ÄéΉΚθ±ΜΫ^Άϊ�����ΓΔ ßΆϊΚΆΑß²ϊΥυΜ\’÷ΒΡΓΑ≤ΓëB(t®Λi)ΒΡïr¥ζΓ±���ΓΘ
±ΨïχΒΡΒΎ“Μ≤ΩΖ÷ΆΗΏ^“Μëπ(zh®Λn)¨Π”Ύëπ(zh®Λn)Κσ20ΡξΒΡ”Αμë¹μΫβΈωΏ@“ΜÜ•ν}��Θ§Ώ@“ΜïrΕΈ±Μ°îïrΒΡ»Υ²ÉΖQûιëπ(zh®Λn)Κσöq‘¬��Θ§Εχ≤Μ «œώΈ“²ÉΫώΧλΥυ’fΒΡΓΑÉ…¥Έ¥σëπ(zh®Λn)÷°ιgΒΡΆΘëπ(zh®Λn)ïrΤΎΓ±�����ΓΘ™QΨδ‘£’f��Θ§±Ψïχ «‘ΎΝμ“Μ¥Έ»Ϊ«ρ–‘¥σëπ(zh®Λn)±§Αl(f®Γ)÷°«Α¨Π1914-1918ΡξΒΡΫβΈωΆΗ“ï����ΓΘΏ@“Μ≤ΩΖ÷ΒΡ÷T’¬Ιù(ji®Π)¨ΔΑ¥μ‰–ρœΒΫy(t®·ng)ΒΊ’™ ω¨è“ï•|öW–¬ΣöΝΔ΅χΦ“ΒΡΏÖΫγÜ•ν}��Θ§“‘ΦΑ¨Π”ΎΉ‘”…Οώ÷ςΒΡΧτëπ(zh®Λn)�ΓΔ÷≥ΟώΒέ΅χΒΡ«ΑΨΑ����ΓΔ άΫγΫ¦ùζΒΡΜλ¹y�ΓΔ÷Ί–¬≈dΤπΒΡΈΡΜ·Ér÷ΒΚΆ΅χκHΚΆΤΫΥυΟφ≈RΒΡΩ²σwÜ•ν}ΓΘ“Μëπ(zh®Λn)ΒΡ≤ΩΖ÷Ώz°a «Ί™ΟφΒΡ����Θ§…θ÷Ν «”–ΚΠΒΡ����Θ§ΒΪ «”––©”Αμë³t «œρΖe‰OΒΡΖΫœρόDΜ·ΘΚ20 άΦo≤Δ≤ΜÉHÉH «“Μ²Ä≥δùMΓΑ≥πΚόΒΡΡξ¥ζΓ±ΓΘ
Ά®Ώ^¨ΠΊû¥©20 άΦoΕΰ»ΐ °Ρξ¥ζΏ@–©÷ςν}ΒΡ’™ ωΚΆΖ÷Έω�Θ§Έ“œκ’fΟςΒΡÜ•ν} «Θ§‘ΎΉν÷Ί“ΣΒΡΖΫΟφ�Θ§¥σ”ΔΒέ΅χ‘Ύ“Μëπ(zh®Λn)÷–ΒΡΫ¦öv≈cöW÷ό¥σξëΒΡΖ®΅χΚΆΒ¬΅χ «≤Μ“Μ‰”ΒΡΘ§Ηϋ≤Μ”Ο’f≈cΕμ΅χΚΆΑΆ†•Η…ΑκçuΒΡ≤ΜΆ§ΝΥ�ΓΘΏ@“≤ «±ΨïχΒΡ÷ς“Σ”^ϋcΓΘ”Δ΅χ‘Ύ“Μëπ(zh®Λn)÷–¦]”–‘β ήΒΫ±ΨΆΝ»κ«÷�Θ§¦]”–‘β ήΒΫ΅ά÷ΊΒΡόZ’®Θ§¦]”–±ΜΨμ»κΒΫΗοΟϋΒΡάΥ≥±÷°÷–��Θ§…θ÷Ν“≤¦]”– ήΒΫÉ»ëπ(zh®Λn)ΚΆΖ«Ζ®ήä ¬±©³”ΒΡθεήk����ΓΘ ¬¨ç…œ����Θ§≥ΐΝΥΟώιgΒΡξP”ΎΩ²ΝTΙΛΚΆΫ¦ùζ¥σΥΞΆΥΒΡ”¦ë¦����Θ§20 άΦoΕΰ»ΐ °Ρξ¥ζΒΡ”Δ΅χüo’™ «‘Ύ’ΰ÷Έ…œΘ§ΏÄ «‘ΎΫ¦ùζ…œ��Θ§ΕΦ±»öW÷ό¥σξëΒΡΡ«–©ύèΨ”²ÉΖÄ(w®ßn)Ε®ΒΟΕύ���ΓΘΒΪ «��Θ§“≤”–“Μ²ÄάΐΆβ����Θ§Ρ«ΨΆ «1916Ρξêέ†•ΧmèΆΜνΙù(ji®Π)ΤπΝx÷°ΚσΒΡΡξ¥ζ���ΓΘêέ†•ΧmξP”Ύ“Μëπ(zh®Λn)ΒΡ”¦ë¦≈c”Δ΅χΒΡ÷ςσw≤ΩΖ÷œύ±»ΗϋΨΏ”–öW÷ό¥σξëΒΡΧΊ’ς���ΓΘ1916-1923Ρξêέ†•ΧmΣöΝΔëπ(zh®Λn)†éΒΡΏz°aΘ§ΥϋΒΡÉ»ëπ(zh®Λn)ΚΆΖ÷κxΒΡÉAœρ��Θ§¨Δ”Αμë20 άΦoΒΡΤδ”ύöq‘¬ΓΘ
“Μëπ(zh®Λn)ΒΡ”Αμë «»Ϊ«ρ–‘ΒΡ���Θ§Υϋ÷Ί–¬Υή‘λΝΥΫϋ•|�����ΓΔ÷≥ΟώΒΊΒΡΖ«÷όΚΆ•|¹ÜΒΊÖ^(q®±)�ΓΘΦ¥ Ι‘ΎΏ@²Ä¨”Οφ…œ�Θ§”Δ΅χΒΡΫ¦öv“≤ «Ζ«Ά§¨Λ≥ΘΒΡΘ§°îΤδΥϊΒέ΅χ‘Ύ“Μëπ(zh®Λn)ΚσΦäΦä±άΥζ÷°κH�����Θ§≤ΜΝ–νç÷°œ¬ΒΡΚΆΤΫΘ®Ώ@”–ϋcœώΖ®ΧmΈςΒέ΅χΘ©Ös‘Ύ1918Ρξ÷°ΚσΏ_ΒΫΝΥ“Μ²ÄμîΖε��ΓΘ»ΜΕχ�Θ§”Δ΅χ‘ΎΑΆά’ΥΙΧΙΚΆΟάΥς≤ΜΏ_ΟΉ¹Ü³ίΝΠΒΡ“βΆβîUèà�����Θ§Ös≥…ûιΥϋ¨Δ¹μΑl(f®Γ)’ΙΒΡ’œΒK�ΓΘ°îëπ(zh®Λn)†éξé”Α‘Ύ30Ρξ¥ζ≥θι_ Φο@§FΒΡïrΚρΘ§“Μëπ(zh®Λn)“≤¨Π”Δ΅χΒΡΖ¥ëΣ°a…ζΝΥ”Αμë���Θ§”Δ΅χ≤ΜÉHÉH «Ά®Ώ^Ϋ½ΨΗ’ΰ≤Ώ¹μ‘΅àDΨS≥÷ΚΆΤΫ�����Θ§Ά§ïr“≤‘ΎûιΩ…ΡήΑl(f®Γ)…ζΒΡëπ(zh®Λn)†éΉωëΣΦ±ΒΡ€ ²δ����ΓΘ°îïrΒΡàΧ(zh®Σ)’ΰ’Ώ÷¬ΝΠ”Ύ”Δ΅χΉ‘…μΖάΩ’σwœΒΒΡ‰΄Ϋ®Θ§Εχ≤Μ «Α―Νμ“Μ≈ζήäξ†ΥΆΒΫöW÷ό¥σξë»Ξ≥δ°î≈ΎΜ“���ΓΘ30Ρξ¥ζΒΡ”Δ΅χ“Μ÷±‘Ύ≈§ΝΠ±ήΟβ“Μàω–¬ΒΡ¥σëπ(zh®Λn)ΒΡ±§Αl(f®Γ)�����ΓΘ“≤’ΐ“ρûι»γ¥Υ��Θ§‘Ύœ¬“Μ¥Έ¥σëπ(zh®Λn)±§Αl(f®Γ)≤Δ«“≥ §F≥ω≈c“Μëπ(zh®Λn)≤ΜΆ§ΒΡëπ(zh®Λn)†é–Έ ΫΒΡïrΚρ����Θ§Ώ@‘Ύ1940ΡξéΉΚθ’ϋΨ»ΝΥ”Δ΅χ���ΓΘ
≈c”Δ΅χœύ±»���Θ§Οά΅χüo’™‘ΎΒΊάμΈΜ÷Ο…œΘ§ΏÄ «‘ΎΨΪ…ώΗ–”X…œΘ§ΕΦΗϋΦ”Ώhκx“Μëπ(zh®Λn)��ΓΘξP”Ύëπ(zh®Λn)†éΨΩΨΙΡήâρéß¹μ ≤Ο¥���Θ§Οά΅χ≤Μîύ‘ωιLΒΡΜΟ€γΗ–÷πùu≈c”Δ΅χΎÖ”Ύ“Μ÷¬����ΓΘΉν÷ς“ΣΒΡ≤ΜΆ§÷ς“Σσw§F”Ύ²ϊΆωΒΡ»ΥîΒ��Θ§”Δ΅χΒΡΥάΆωΩ²îΒ «72Σ±3»f»Υ��Θ§Οά΅χ³t «11Σ±6»f»ΥΓΣΓΣΕχΤδ÷–≥§Ώ^ΑκîΒΒΡΥάΆω «”…”Ύ1918ΡξΒΡ¥σΝςΗ–�����ΓΘ8¨Π”ΎΟά΅χ»ΥΕχ―‘�����Θ§ΓΑ¥σëπ(zh®Λn)Γ±ëΣ‘™ «1861-1865ΡξΒΡΟά΅χÉ»ëπ(zh®Λn)�����Θ§Ι≤”–62»f»ΥΥά”ΎΏ@àωΩ…≈¬ΒΡÉ»ëπ(zh®Λn)���Θ§Ώ@²ÄîΒΉ÷±»É…¥Έ¥σëπ(zh®Λn)ΤΎιgΟά΅χΥάΆω»ΥîΒΦ”Τπ¹μΏÄ“ΣΕύ�ΓΘ¨Π”ΎΟά΅χ»Υ¹μ’f���Θ§Υϊ²ÉΫι»κ“Μëπ(zh®Λn)ΒΡïrιgΕΧïΚ��Θ§™p ßΈΔ–Γ����Θ§Υυ“‘“Μëπ(zh®Λn)ΚήΩλΨΆ±Μ1941-1945ΡξΒΡΕΰëπ(zh®Λn)≈cΤδΚσΒΡάδëπ(zh®Λn)Υυ¦_Β≠ΝΥ���ΓΘ»ΜΕχ���Θ§’ΐ «”…”Ύ“Μëπ(zh®Λn)Θ§Οά΅χΒΎ“Μ¥Έ±»ί^…ν»κΒΊΫι»κΝΥöW÷όΒΡ¦_ΆΜ���Θ§≤Δ“‘¥Υ≤Ϋ»κΝΥ»Ϊ«ρΆβΫΜ��ΓΘ¨ΠΟά΅χνI¨ß»ΥΕχ―‘���Θ§Ώ@ΖNΫ¦öv¨Δ≥…ûι20 άΦoΟά΅χΆβΫΜΒΡ“Μ²Ä‰Υ½UΘ§”»Τδ «°îΥϊ²ÉΗ–ΒΫΉςûι“Μ²Ä άΫγ–‘ΒΡ¥σ΅χΟφ≈R’ΰ÷ΈΊ™™ζΚΆΨΪ…ώάßΨ≥ΒΡïrΚρ���ΓΘ
ΓΓΓΓ“Μëπ(zh®Λn)ΒΡ”ΑμëΖ«≥ΘèVΖΚ�����Θ§≤Δ«“Ίû¥©ΝΥ’ϊ²Ä20 άΦoΒΡ20Ρξ¥ζΚΆ30Ρξ¥ζ���ΓΘΒΪ «Ώ@àω±ΜΖQûιΓΑΫKΫYΥυ”–ëπ(zh®Λn)†éΒΡëπ(zh®Λn)†éΓ±ΒΡ“βΝx±ΜèΊΒΉΆΤΖ≠ΝΥ����Θ§“ρûι≤ΜΒΫΥΡΖ÷÷°“Μ άΦo÷°ΚσΨΆ±§Αl(f®Γ)ΝΥΒΎΕΰàωΗϋΩ÷≤άΒΡ¥σëπ(zh®Λn)���ΓΘ‘ΎΕΰëπ(zh®Λn)÷–�����Θ§”Δ΅χ‘βΒΫΝΥ΅ά÷ΊΒΡόZ’®����Θ§Οφ≈R÷χΤ»‘ΎΟΦΫόΒΡ«÷»κ”Δ΅χ±ΨΆΝΒΡΆΰΟ{�Θ§Υϋ‘Ύ¹Ü÷όΒΡ÷≥ΟώσwœΒ“≤±ΜΏ@àωëπ(zh®Λn)†éèΊΒΉνçΗ≤ΝΥ�ΓΘ20 άΦoΕΰ»ΐ °Ρξ¥ζ±ΜΖQûιΓΑÉ…¥Έ άΫγ¥σëπ(zh®Λn)ΒΡιg–ΣΤΎΓ±Θ§1914-1918ΡξΒΡëπ(zh®Λn)†é“≤“ρ¥Υ±ΜΖQûιΓΑΒΎ“Μ¥Έ άΫγ¥σëπ(zh®Λn)Γ±�ΓΘ‘Ύëπ(zh®Λn)Κσ’ϊ’ϊ20ΡξΒΡïrιgάο��Θ§“Μëπ(zh®Λn)ΒΡ“βΝx±ΜΕΰëπ(zh®Λn)ΚΆάδëπ(zh®Λn)Υυ―Ύ…w�����Θ§“ρûιΥϋ²Ééß¹μΝΥΗϋΩ÷≤άΒΡΆάöΔΚΆόZ’®����ΓΘ“Μëπ(zh®Λn)Ér÷ΒΒΡ÷Ί–¬Αl(f®Γ)Ψρ «‘Ύ20 άΦo60Ρξ¥ζ�Θ§“≤ΨΆ «Ψύκx“Μëπ(zh®Λn)¥σΦs50ΡξΒΡïrΚρΓΘ¨Π”Ύ”Δ΅χ»ΥΕχ―‘���Θ§’ΐ «‘ΎΏ@“ΜïrΤΎ����Θ§1914-1918Ρξ≥…ûιΝΥ“Μ²ÄΙ ¬ΒΡ–Έ Ϋ�����Θ§Εχ«“÷ς“Σ «ξP”Ύëπ(zh®Λn)ΚΨΚΆ‘ä»ΥΒΡΙ ¬��ΓΘ
1945Ρξ÷°Κσ�����Θ§1914-1918ΡξΒΡ“Μëπ(zh®Λn)‘λ≥…ΒΡ÷±Ϋ”ΒΡΈοΌ|¨”ΟφΒΡ”Αμë“―Ϋ¦œϊ ßΝΥΘ§ΒΪ «ξP”ΎΏ@ΕΈöv ΖΒΡ”¦ë¦ΖΫ ΫÖsΉÉΒΟΗϋΦ”÷Ί“Σ�Θ§»ΜΕχΏ@Ös «±Μ°î¥ζ»ΥΒΡ”^ΡνΥυΥή‘λΒΡöv ΖΓΘάΐ»γ�����Θ§‘Ύ20 άΦo60Ρξ¥ζΒΡïrΚρ��Θ§”Δ΅χ±§Αl(f®Γ)ΒΡΡξίp»ΥΖ¥ΩΙ±Θ ΊΒΡ°îôύ≈…ΒΡ‘λΖ¥Ώ\³”ΚΆ“―Ϋ¦‘ΎΒ¬΅χ±§Αl(f®Γ)ΒΡΖ¥¨ΠΓΑ≥ΝΡ§ΒΡ“Μ¥ζΓ±ΒΡΜν³”����Θ§Τδ––ûιΆ§Φ{¥β³eüoΕΰ÷¬ΓΘΕχΒΫΝΥΫϋ–©Ρξ�Θ§‘ΎΤ’±ιΒΡ΅χκH¨”Οφ…œΘ§¨Π“Μëπ(zh®Λn)ΒΡΩ¥Ζ®³tΗϋΦ” ήΒΫάδëπ(zh®Λn)ΒΡ”Αμë����ΓΘΏ@‘ΎξP”ΎΥςΡΖΚ”ëπ(zh®Λn)“έΓΔΩ®≤®άΉΆ–ëπ(zh®Λn)“έΚΆΩΩΫϋ“ΝΤ’†•ΒΡêέ†•ΧmΚΆΤΫΥΰΒΡÜ•ν}…œο@ΒΟ”»ûιΆΜ≥ω����ΓΘ°î»ΜΘ§”Δ΅χξP”ΎΏ@àωëπ(zh®Λn)†é¦_ΆΜΒΡΩ¥Ζ®÷ς“ΣΦ·÷–”ΎΥςΡΖΚ”ëπ(zh®Λn)“έ��ΓΘ‘Ύ±ΨïχΒΡΒΎΕΰ≤ΩΖ÷����Θ§‘Ύ“ΜœΒΝ–Α¥’’ïrιgμ‰–ρ‘O”΄ΒΡ’¬Ιù(ji®Π)άοΘ§Έ“²ÉΉΖΥίΝΥ1914-1918Ρξ¨Π”Ύ20 άΦoœ¬Ακ»~°a…ζΒΡ”Αμë�����Θ§ΕχΏ@ΖN”Αμëκm»Μ‘Ύ°îïr¦]”–÷±Ϋ”ο@§F≥ω¹μ�����Θ§ΒΪ «»‘»Μ’έ…δ”ΎΤδΚσΒΡ άΫγ���Θ§ Ήœ» «Ά®Ώ^1939-1945ΡξΕΰëπ(zh®Λn)ΒΡάβγRο@ Ψ≥ω¹μ��Θ§ΤδΚσΗϋ «Ά®Ώ^1989-1991Ρξάδëπ(zh®Λn)ΒΡΫYΨ÷ο@ Ψ≥ω¹μ���Θ§Ά§ïrάδëπ(zh®Λn)ΒΡΫY χ“≤‰Υ÷Ψ÷χΉ‘1945Ρξ“‘¹μëπ(zh®Λn)ΚσïrΤΎΒΡΫKΫYΓΘ‘ΎΏ@–©’¬Ιù(ji®Π)άο��Θ§Έ“¨ΔΑ―¥σΦ“ λœΛΒΡïχΦ°�����ΓΔκä”ΑΚΆ ¬ΦΰΏM––κSôCΒΡΫMΚœ�����Θ§èΡΕχΒΟ≥ωΉÉ³”ΒΡ§F¨ç‘Ύ±ΨΌ|…œ «öv ΖΒΡ≤Μîύ‘Ό§FΒΡ”^ϋcΓΘ
ΓΓΓΓ“ρ¥Υ����Θ§±Ψïχ¨Π”Ύ“Μëπ(zh®Λn)ΒΡΖ÷Έω≤ΜÉHÉH «ûιΝΥΤ Έω1914-1918ΡξΒΡöv ΖΏz°aΘ§Εχ«““≤ «ûιΝΥΫβα¨20 άΦo“Μëπ(zh®Λn)ΚσΒΡöq‘¬ΒΡΡ≥–©÷Ί“ΣΧΊ’ς����ΓΘΏ@–©’¬Ιù(ji®Π)ΒΡΖΕ΅ζΖ«≥ΘèVΖΚΘ§ΑϋΚ§ΝΥΚήΕύöv Ζ¨WΒΡΖ÷÷ߨWΩΤ����Θ§Φ»Αϋά®ήä ¬öv ΖΘ§”÷…φΦΑΈΡΜ·―–ΨΩ���ΘΜΦ»ΧΫ”ë“βΉR–ΈëB(t®Λi)Ü•ν}�����Θ§”÷ΧNΚ§Ϋ¦ùζ¨WΒΡÉ»»ί��ΘΜΆ§ïr“≤ξPΉΔöv Ζ¨WΩΤΒΡΉν–¬―–ΨΩΎÖ³ί��ΓΘΕχ÷ΝξP÷Ί“ΣΒΡ «��Θ§Ά®Ώ^Α―”Δ΅χ»Υ‘Ύ“Μëπ(zh®Λn)÷–ΒΡΫ¦öv÷Ο”ΎöW÷ό’ZΨ≥÷–ΏM––”^≤λ�Θ§Έ“œΘΆϊΡήâρΏ_ΒΫΏ@‰”“Μ²ÄΡΩ‰ΥΘΚ²ςΫy(t®·ng)ΒΡ���ΓΔ“‘”ΔΗώΧmûι÷––ΡΒΡξP”Ύëπ(zh®Λn)†éΒΡ”^Ρν����Θ§ «Τ»«––η“ΣΦ”“‘–ό’ΐΒΡ�����ΓΘΚÜΕχ―‘÷°����Θ§Έ“‘΅àDΫβα¨Ώ@‰”“Μ²ÄÜ•ν}Θ§Ρ«ΨΆ «ûι ≤Ο¥”Δ΅χ»ΥξP”Ύ“Μëπ(zh®Λn)ΒΡΩ¥Ζ®≥ω§FΝΥΤΪ≤ν≈cÜ•ν}����ΓΘ
ΓΓΓΓΫβ¦QΏ@²ÄÜ•ν}ΒΡ“Μ²Ä”––ßΒΡΆΨèΫΘ§ΨΆ «“ΣîU’ΙΈ“²É¨Π”Ύëπ(zh®Λn)†éΒΡΡξ±μΒΡ’JΉRΚΆΗ–”X�����ΓΘ”Δ΅χ»Υ¨Π”Ύ“Μëπ(zh®Λn)ΒΡ”^Ρν÷ς“ΣΦ·÷–”Ύ1916ΡξΘ§Ηϋ¥_«–ΒΊ’f��Θ§ «Φ·÷–‘Ύ1916ΡξΒΡ7‘¬1»’��Θ§“≤ΨΆ «÷χΟϊΒΡΥςΡΖΚ”ëπ(zh®Λn)“έ±§Αl(f®Γ)ΒΡΡ«“ΜΧλ�����ΓΘΒΪ¨çκH…œ��Θ§ëπ(zh®Λn)†é≥÷άm(x®¥)ΝΥΥΡΡξΒΡïrιg���Θ§Ζ÷ûιéΉ²ÄκAΕΈ��ΓΘ»γΙϊΈ“²Éœκ“Σ≥δΖ÷άμΫβ“Μëπ(zh®Λn)¨Π”Ύëπ(zh®Λn)ΚσéΉ °ΡξΒΡ”Αμë���Θ§ΉνΚσ“ΜΡξ «÷ΝξP÷Ί“ΣΒΡΘ§»ΜΕχ«Γ«ΓΏ@“ΜΡξ «Ήν“Ή±ΜΚω“ïΒτΒΡ“ΜΡξ�ΓΘ¨Π”Ύ±ΨïχΕχ―‘Θ§“Μëπ(zh®Λn) «»γΚΈΫY χΒΡΏhΏh±»Υϋûι ≤Ο¥ι_ ΦΗϋΦ”÷Ί“Σ����ΓΘΕχ“Μëπ(zh®Λn)ΚσΙϊΒΡο@§FΘ§νêΥΤ”ΎΟΆΝ“ΒΡâΚΝΠ‘ΎΤδΚσîΒ °ΡξΒΡΫ©Ψ÷÷–ΒΟ“‘±§Αl(f®Γ)≥ω¹μ��ΓΘ
ΓΓΓΓëπ(zh®Λn)†éΒΡ≥θΦâκAΕΈ÷ς“ΣΦ·÷–”Ύ1914ΡξΓΘΈ“²ÉΏ@άο≤ΜΧΫ”ë‘Ύ¥Υ÷°«ΑΒΡΨoèà†νëB(t®Λi)ΒΡ”Αμë���Θ§ΒΪ «7‘¬ΈΘôC «“βΝœ÷°ΆβΒΡ ¬«ι����Θ§ΕχΥϋÖs≥…ûι“Μëπ(zh®Λn)ΒΡ¨ßΜπΥς��ΓΘΏ@άοΒΡÜ•ν} «���Θ§’l¨Δûι“Μëπ(zh®Λn)ΒΡ±§Αl(f®Γ)Ί™Ίü»ΈΘ§Μρ’Ώ’fΡΡ“Μ²Ä΅χΦ“¨ΔΊ™÷ς“ΣΊü»Έ���Θ§Ώ@¨Δ‘ΎΏ@±Ψïχ÷–÷π≤ΫΒΊ±ΜΆΤ¨ß≥ω¹μ���ΓΘ≥δΖ÷ΒΡΉC™ΰ±μΟςΘ§Ιΰ≤ΦΥΙ±ΛΒέ΅χ «÷ς“ΣΒΡΊü»Έ΅χ�����Θ§ΕχΥϋΒΡΆβΫΜ’ΰ≤ΏΏx™ώ����Θ§“ΜΖΫΟφ «“ρûι ήΒΫΝΥΆΜ»Μ¥ΧöΔ ¬ΦΰΒΡ”ΑμëΘ§Νμ“ΜΖΫΟφ «“ρûιΒΟΒΫΝΥΒ¬΅χΜ ΒέΆΰΝ°ΒΡ÷ß≥÷ΓΘ”Ύ «Υϋ‘΅àD“Μ³Ύ”ά“ίΒΊΫβ¦QΫ¦≥ΘΫoΥϋ÷Τ‘λ¬ιü©ΒΡύè΅χ»ϊ†•ΨS¹ÜÜ•ν}����ΓΘΚήΩλΘ§÷ß≥÷»ϊ†•ΨS¹ÜΒΡ…≥Μ Εμ΅χ±ΜΨμ»κΝΥëπ(zh®Λn)†é��Θ§κSΚσ…≥Μ Εμ΅χΒΡΟΥ”―Ζ®ΧmΈςΙ≤ΚΆ΅χ“≤Ϋι»κΝΥ����ΓΘ‘ΎΫ¦Ώ^ΦΛΝ“ΒΡ†é’™÷°ΚσΘ§”Δ΅χ°î’ΰΒΡΉ‘”…ϋh’ΰΗ°Α―ΥϋΒΡΟϋΏ\ΚΆΖ®΅χ“‘ΦΑ±»άϊïr¬™œΒ‘ΎΝΥ“ΜΤπ�Θ§“ρûι±»άϊïr“Μ÷±ë©«σ”Δ΅χ±Θ’œΥϋ‘Ύëπ(zh®Λn)†é÷–ΒΡ÷–ΝΔΒΊΈΜΓΘ‘Ύ1914ΡξΫ”œ¬¹μΒΡïrιgάο�����Θ§Αl(f®Γ)…ζΝΥΚήΕύ ¬«ι���Θ§ΕχΏ@–© ¬«ιΆ®≥ΘΕΦ±Μ»Υ²ÉΏzΆϋΝΥ�����ΓΘΏ@“ΜΡξëπ(zh®Λn)†é“é(gu®©)ΡΘ―ΗΥΌîU¥σ���Θ§Ζ®΅χΒΡήäξ†ΆΤΏMΒΫΑΔ†•Υ_ΥΙΚΆ¬εΝ÷��Θ§…≥Εμήäξ†ΏM»κΝΥ•|Τ’τî ΩΒΊÖ^(q®±)�Θ§Β¬΅χ³t―ΗΥΌΒΊœρΑΆάηΆΤΏM��ΓΘΗςΫΜëπ(zh®Λn)΅χ’ΰΗ°ΕΦ’Jûιïΰ―ΗΥΌΒΊ»ΓΒΟ“Μàω¦QΕ®–‘ΒΡ³Όάϊ����Θ§ΒΪ «ëπ(zh®Λn)¦rΒΡΑl(f®Γ)’Ι ΙΒΟΥϋ²ÉüoΖ®Ώ_ΒΫΏ@–©≤ΜΆ§ΒΡΡΩ‰ΥΘ§Ηϋûι΅άΨΰΒΡ «��Θ§Υϋ²ÉΕΦΒΆΙάΝΥ§F¥ζ≈Ύ±χΚΆôCξP‰¨¨Π”Ύ≤Ϋ±χ≤Ωξ†ΒΡΨό¥σöΔ²ϊΝΠ����ΓΘ¨Π”ΎΫΜëπ(zh®Λn)κpΖΫΒΡ¥σ≤ΩΖ÷΅χΦ“Εχ―‘����Θ§1914Ρξήäξ†ΒΡ²ϊΆω¬ «“Μëπ(zh®Λn)÷–ΉνΗΏΒΡ“ΜΡξΘ§άΐ»γ���Θ§Ζ®΅χΒΡ²ϊΆω»ΥîΒΏ_ΒΫΝΥ50»f��ΓΘ1914Ρξ8‘¬22»’ «Ήνûι΅άΨΰΒΡ“ΜΧλ����Θ§Ζ®΅χήäΎΏMΙΞΒΡΏ^≥Χ÷–™p ßΝΥ2Σ±7»f»ΥΘ§Ώ@²ÄîΒΉ÷±»”Δ΅χ‘ΎΥςΡΖΚ”ëπ(zh®Λn)“έΒΎ“ΜΧλΒΡ²ϊΆω»ΥîΒ“ΣΕύΒΟΕύ�ΓΘ‘ΎΒ¬΅χΏMΙΞΖ®΅χξ΅ΒΊΒΡïrΚρΘ§Ζ®΅χ Ω±χ“ρûιήäΖΰν¹…ΪΘ®Υ{…ΪΒΡ χ―ϋ…œ“¬ΚΆΦt…ΪΒΡ―ùΉ”Θ©Ζ«≥ΘθrΤG���Θ§ΕχΖ«≥Θ»ί“ΉΒΊ≥…ΝΥΒ¬΅χôCξP‰¨ΒΡΑ–Ή”��ΓΘ
ΓΓΓΓ1915Ρξ�����Θ§Ές≤Ωëπ(zh®Λn)ΨÄ“―Ϋ¦ΏM»κΝΥ¬ΰιLΒΡΒΎΕΰκAΕΈ�Θ§Ώ@“ΜκAΕΈ�Θ§èΡ»π ΩΒΫ±±ΚΘΘ§¨”¨”ΒΡëπ(zh®Λn)ΚΨ±ΜΆΎΨρ≥ω¹μ��Θ§¨çκH…œ“≤ «ΏM»κΝΥ±äΥυ÷ή÷ΣΒΡœύ≥÷κAΕΈ����Θ§Ά§ïrΥϋ“≤ «“Μ²Ä―ΣΝς≥…Κ”ΒΡœύ≥÷κAΕΈΓΘΫΜëπ(zh®Λn)κpΖΫΒΡΥυ”–΅χΦ“»‘»ΜΜΟœκ‘Ύëπ(zh®Λn)àω…œΡήâρ»ΓΒΟ“Μàω¦QΕ®–‘ΒΡ³Όάϊ���Θ§èΡΕχèΊΒΉΗυ≥ΐî≥»Υά^άm(x®¥)ëπ(zh®Λn)†éΒΡ‘ΗΆϊ�����ΓΘ”Δ΅χΚΆΖ®΅χ‘΅àDΆ®Ώ^ΙΞ™τΒ¬΅χΒΡΟΥ΅χäWΥΙ¬ϋΒέ΅χ¨ç§FΏ@“ΜΡΩ‰Υ�ΓΘ¨ΠäWΥΙ¬ϋΒέ΅χΒΡΏMΙΞΑl(f®Γ)…ζ‘Ύ1915Ρξ4‘¬Θ§»ΜΕχΑl(f®Γ)…ζ‘ΎΦ”άο≤®άϊΒΡΏ@àωëπ(zh®Λn)“έΒΡΫYΨ÷ «ûΡκy–‘ΒΡ����ΓΘ5‘¬Θ§“β¥σάϊ±ß÷χΆ§‰”ΒΡœΘΆϊΑl(f®Γ)³”ΝΥ¨ΠäW–ΌΒέ΅χΒΡΏMΙΞ�Θ§ΒΪ «Ös±Μάß‘ΎΝΥΑΔ†•±ΑΥΙ…ΫΓΘ1915Ρξ�Θ§Β¬΅χΒΡΏM’ΙΗϋûιμ‰άϊ“Μ–©Θ§“‘³ί≤ΜΩ…°îΒΡÉû(y®≠u)³ίëπ(zh®Λn)³ΌΝΥ»ϊ†•ΨS¹Ü�����Θ§≤Δ«“èΡ…≥ΕμΡ«άοΨπ»ΓΝΥ≤®ΧmΒΡ¥σ≤ΩΖ÷νIΆΝ���Θ§»ΜΕχΏ@–©³Όάϊ“≤¦]”–Ώ_ΒΫ÷¬Οϋ“Μ™τΒΡ–ßΙϊΘ§…≥Μ Εμ΅χΒΡ Ωöβ»‘»ΜΚήΖÄ(w®ßn)ΙΧ��ΓΘ¨çκH…œ�����Θ§“Μëπ(zh®Λn)«ΑΑκΕΈΒΡ“Μ²ÄΖ«≥Θ÷Ί“ΣΒΡΧΊ’ςΨΆ «ëπ(zh®Λn)†éΚσΖΫΤπ÷χ÷ΝξP÷Ί“ΣΒΡΉς”Ο�Θ§Ώ@≈cëπ(zh®Λn)«ΑΒΡ¨Π”Ύ…γïΰ÷ςΝxΚΆΚΆΤΫ÷ςΝxΒΡΩ÷ë÷ «ΫΊ»ΜœύΖ¥ΒΡ�ΓΘ°îëπ(zh®Λn)†éΒΡ¥ζÉrΗΏΑΚïr�Θ§ΚΆΤΫΒΡ¥ζÉr“≤ «»γ¥ΥΓΘ’ΐ»γ“Μ²ÄΒ¬΅χ¥σ≥Φ‘Ύ1914Ρξ11‘¬Υυ’fΒΡΡ«‰”��Θ§‘ΎΗΕ≥ωΝΥ»γ¥ΥΗΏΑΚΒΡ¥ζÉrΚΆΩ÷≤άΒΡ†ό…ϋ÷°Κσ�����Θ§÷Μ”–Ος¥_ΒΡ³ΌάϊΥΤΚθ≤≈ «Ω…“‘Ϋ” ήΒΡ���Θ§ΤδΥϊ»ΈΚΈΒΡΫYΨ÷¨Π”Ύ»ΥΟώ¹μ’fΕΦ «≤Μ≥δΖ÷ΒΡ����ΓΘ
ΓΓΓΓïrιgΆΤΏMΒΫΝΥ1916Ρξ�����Θ§ΫΜëπ(zh®Λn)κpΖΫ»‘»Μ“Μ÷±±ß÷χΏ@‰”ΒΡœΘΆϊ����Θ§Φ¥“Μàω¦QΕ®–‘ΒΡëπ(zh®Λn)“έΡήâρ»ΓΒΟΉνΫKΒΡ³ΌάϊΘ§≤Δûι¥ΥΉωΚΟΝΥ––³”…œΒΡ€ ²δΙΛΉς����ΓΘ¥σΕύîΒΫΜëπ(zh®Λn)΅χΑ―GDPΒΡ“ΜΑκ“‘…œ”ΟΒΫΝΥήä ¬Ζά”υ…œ��ΓΘΗς΅χ’ΰΗ°÷πùu“βΉRΒΫΫ¦ùζΚΆ…γïΰ‘Ύëπ(zh®Λn)†é÷–ΒΡΉς”Ο����Θ§Ώ@ΖNΖΫ Ϋ“≤±ΜΖQûιΓΑΩ²σwëπ(zh®Λn)Γ±��ΓΘΗς΅χΦäΦäèäΜ·ΝΥ’ΰ÷Έ…œΒΡΩΊ÷ΤÉAœρ����ΓΘ‘ΎΒ¬΅χΘ§1914ΡξΒΡ’ΰ÷Έ…œΒΡ“Μ÷¬≤ΜèΆ¥φ‘Ύ�Θ§≥÷≤ΜΆ§’ΰ“äΒΡ…γïΰ÷ςΝx’ΏΙΪι_Ζ¥¨ΠΒέ΅χ÷ςΝxëπ(zh®Λn)†éΓΘ”Δ΅χèä÷Τ–‘ΒΊΆΤ––’ς±χ’ΰ≤Ώ�Θ§Ώ@Ώ`Ζ¥ΝΥ…ώ ΞΒΡΉ‘”…‘≠³tΘ§“‘¥σ–l(w®®i)·³ΎΚœ·ÜΧ÷Έûι ΉœύΒΡ–¬ΒΡ¬™Κœ’ΰΗ°≥…ΝΔ�Θ§≤Δ«“ΏM––ΝΥά^άm(x®¥)ëπ(zh®Λn)†éΒΡ≈§ΝΠΓΘ‘Ύëπ(zh®Λn)àω…œ�����Θ§Β¬΅χΉνΗΏΫy(t®·ng)é¦≤ΩΑ―ΡΩ‰ΥφiΕ®‘ΎΖ≤†•Β«ΒΊÖ^(q®±)���Θ§œΘΆϊ‘ΎΏ@“ΜΒΊÖ^(q®±)ΓΑΉ¨Ζ®΅χ»ΥΒΡ―ΣΝςΗ…Γ±Θ§ΒΪ «Ώ@“Μëπ(zh®Λn)“έ ßîΓΝΥ���Θ§Β¬΅χήäξ†≈cΖ®΅χήä̉”―ΣΝς≥…Κ”�����ΓΘΖ≤†•Β«ëπ(zh®Λn)“έΤΎιg����Θ§ΫΜëπ(zh®Λn)κpΖΫΒΡΥάΆω»ΥîΒΙά”΄‘Ύ40»f~60»fΓΘΨΪ¥_ΒΡîΒΉ÷Ϋy(t®·ng)”΄ «≤ΜΩ…ΡήΒΡ��Θ§“ρûι‘SΕύ Ω±χΕΦ±Μ’®≥…ΝΥΥιΤ§�����Θ§÷ΝΫώ»‘»ΜΩ…“‘‘ΎΕ≈äWΟ…‘α §ΧΟάοΩ¥ΒΫèΡëπ(zh®Λn)àω…œΥ―Φ·ΒΫΒΡ¥σΝΩΥιΙ«�ΓΘûιΝΥΫβΨ»Ζ≤†•Β«άßΨ÷Θ§Öf(xi®Π)Φs΅χ‘ΎΥςΡΖΚ”Αl(f®Γ)ΤπΝΥΏMΙΞ�����ΓΘΒΪ «”Δ΅χ‘ΎΒΎ“ΜΧλΨΆ™p ßΝΥ60»f»Υ���Θ§Τδ÷–ΒΡ1/3 «±ΜöΔΥάΒΡ����Θ§”Ύ «1916Ρξ7‘¬1»’¨Π”Ύ”Δ΅χ»Υ¹μ’f≥…ΝΥëπ(zh®Λn)†é÷–ΉνΩ…≈¬ΒΡ“ΜΧλΓΘ»ΜΕχ�����Θ§Ώ@àωΏMΙΞ»‘»Μ≥÷άm(x®¥)ΒΫΝΥ11‘¬���Θ§“ρûι°îïrΒΡëπ(zh®Λn)ΒΊΫy(t®·ng)é¦ΒάΗώά≠ΥΙ·ΚΎΗώ»‘»ΜΦΡœΘΆϊ”ΎΡήâρ”–“Μ²Äëρ³Γ–‘ΒΡΆΜΤΤ���ΓΘ‘Ύ’ϊ²ÄΥςΡΖΚ”ëπ(zh®Λn)“έΤΎιgΘ§”Δ΅χΒΡ²ϊΆω»ΥîΒΏ_ΒΫΝΥ42»f»Υ�����Θ§Ζ®΅χΒΡ²ϊΆω»ΥîΒ¥σΦs «Ώ@²ÄîΒΉ÷ΒΡ“ΜΑκ����Θ§Ά§‰”Θ§Β¬΅χΒΡ™p ß“≤ «Ψό¥σΒΡ���Θ§ΤδîΒΉ÷Ω…ΡήΫ”Ϋϋ”Ύ”Δ΅χΚΆΖ®΅χΒΡΩ²ΚΆ����ΓΘ
ΓΓΓΓ1916Ρξ11‘¬13»’���Θ§°îïrΒΡΥςΡΖΚ”ΙΞ³ί“―Ϋ¦“ρûιΕ§ΧλΒΡ¹μ≈RΕχ€p»θΝΥ�����Θ§”Δ΅χΒΡ«ΑΆβΫΜ¥σ≥ΦΧmΥΙΕύΕς³ΉΨτΫ®Ήh”Δ΅χÉ»ιwΩΦë]ΚΆΤΫ’³≈–ΒΡÜ•ν}���ΓΘΓΑηb”ΎΡΩ«ΑΒΡ»ΥΩΎ²ϊΆω�����ΓΔΫπ»Ύ™p ßΚΆ¨Π…ζ°aΝΠΒΡΤΤâΡ�����Θ§ëπ(zh®Λn)†é™p ßΒΡΜ÷èΆΩ…Ρή–η“ΣéΉ¥ζ»ΥΒΡïrιgΓ±�Θ§²ϊΆω»ΥîΒ“―Ϋ¦Ώ_ΒΫΝΥ100»fΘ§”Δ΅χΟΩΧλΒΡëπ(zh®Λn)†éΜ®ΌMΕΦΏ_ΒΫ500»f”Δφ^�����Θ§ΓΑΏ@¥_¨ç «Έ“²ÉëΣ‘™≥– ήΒΡΊü»ΈΓ±��Θ§ΓΑΒΪ «÷Ν…ΌëΣ‘™Ή¨Έ“²ÉΩ¥ΒΫΈ“²ÉΒΡ†ό…ϋ «ïΰ”–ΜΊàσΒΡΘ§»γΙϊΥυ”–ΒΡΗΕ≥ωΕΦ «ΆΫ³ΎΒΡ���Θ§»γΙϊ‘Ό”–“ΜΡξ��ΓΔÉ…ΡξΜρ’Ώ»ΐΡξ���Θ§Έ“²ÉΑl(f®Γ)§FΈ“²É»‘»ΜüoΖ®Ϋβ¦QÜ•ν}Θ§Ρ«Ο¥ëπ(zh®Λn)†éΒΡ―”ιLΚΝüo“βΝx�ΓΘΡ«–©ΏM––ΚΝüo“βΝx―”ιLëπ(zh®Λn)†éΒΡ»ΥΒΡΊü»Έ≤Δ≤Μ±»Αl(f®Γ)³”ëπ(zh®Λn)†éΒΡ»ΥΒΡΊü»Έ“Σ–ΓΓ±ΓΘ°îΨ÷’Ώ¨ΠΧmΥΙΕύΕς³ΉΨτΒΡΫ®Ήh≥δΕζ≤Μ¬³�����Θ§ΒΪΥϊΧα≥ω¹μΒΡÜ•ν}��Θ§Εχ«“?gu®©)ΉΚθΨΆ «‘ΎΉνΫKΒΡΆΘëπ(zh®Λn)Öf(xi®Π)Ε®Ώ_≥…ΒΡÉ…Ρξ«ΑΆ§“ΜΧλΒΡïrιgΧα≥ω¹μΒΡΏ@²ÄÜ•ν}�Θ§Φ¥ΥϊΥυξU ωΒΡά^άm(x®¥)ëπ(zh®Λn)†ééß¹μΒΡΚσΙϊΏ@“Μ”^ϋcΘ§“≤“Μ÷±Ή¨”Δ΅χ»Υ±Ε ή’έΡΞ���ΓΘ14
ΓΓΓΓ1916Ρξ���Θ§ΟΩ“ΜΖΫΑl(f®Γ)³”ΒΡΙΞ™τΘ®üo’™Ζ≤†•Β«Θ§ΏÄ «ΥςΡΖΚ”Θ©ΕΦ ßîΓΝΥ�����Θ§≤Δ«“ΕΦΗΕ≥ωΝΥΨό¥σΒΡ¥ζÉrΘ§Ά§ïr΅χÉ»ΒΡρ}³”“≤‘Ύëπ(zh®Λn)†éΚσΖΫΫoΥϋ²É ©Φ”ΝΥΚή¥σΒΡâΚΝΠ���ΓΘ1917ΡξΘ§Ν―Ωpι_ Φ≥ω§F�Θ§ëπ(zh®Λn)†éΏM»κΝΥ“Μ²ÄΗϋΦ”≤ΜΖÄ(w®ßn)Ε®ΒΡΒΎ»ΐκAΕΈΓΘΒ¬΅χ»ΥΩsΕΧΝΥΥϊ²ÉΒΡΈς≤Ωëπ(zh®Λn)ΨÄ��Θ§≥ΖΜΊΒΫ–¬Φ”ΙΧΒΡΖά”υΙΛ ¬÷–»Ξ���ΓΘΟά΅χ»‘»Μ±Θ≥÷÷χ÷–ΝΔΒΡëB(t®Λi)Ε»�Θ§ΒΪ «”Δ΅χΏM––ëπ(zh®Λn)†éΒΡ–η«σΗϋΦ”“άΌ΅”Ύ¥σΈς―σ±ΥΑΕΒΡΟά΅χ����Θ§≤Δ«“ΌYΫπ÷ς“Σ¹μ‘¥”ΎΟά΅χψy––ΚΆΥΫ»ΥΆΕΌY’ΏΒΡΌJΩνΓΘ“ρ¥Υ��Θ§Β¬΅χΉνΗΏΫy(t®·ng)é¦≤ΩΉω≥ωΝΥ“Μμ½÷Ί¥σ¦QΕ®���Θ§¦QΕ®‘Ύ¥σΈς―σΑl(f®Γ)³”≤Μ ήœό÷ΤΒΡù™Άßëπ(zh®Λn)�Θ§¥Υ≈eΑ―Οά΅χΆœ»κΝΥëπ(zh®Λn)†é�����ΓΘΒ¬΅χ»Υ’JûιΘ§‘ΎΟά΅χΏM––≥δΖ÷ΒΡëπ(zh®Λn)†é³”ÜT÷°«Α�����Θ§Υϊ²ÉΒΡù™ΆßΡήâρèΊΒΉ«–îύ”Δ΅χΩγ¥σΈς―σΒΡΙ©ëΣΨÄ��Θ§‘ΎΕΧïrΤΎÉ»��Θ§Β¬΅χ»ΥΒΡëπ(zh®Λn)¬‘ΥΤΚθ»ΓΒΟΝΥ≥…ΙΠ���ΓΘ1917Ρξ4‘¬�����Θ§Ζ®΅χήäξ†Αl(f®Γ)…ζΝΥ±χΉÉ�Θ§÷ς“Σ¨ßΜπΥς «‘ΎΌF΄D–ΓèΫΏ@“ΜΒΊÖ^(q®±)Αl(f®Γ)³”ΝΥ¨ΠΒ¬΅χ»ΥΒΡΉ‘öΔ–‘“u™τ��ΓΘ»γΙϊ≤Μ «“ρûι÷Η™]ΙΌΝ_≤°ΧΊ·ΡαΨS†•ΑΝ¬ΐΉ‘Ί™����Θ§Ζ®΅χήäξ†…θ÷ΝΩ…“‘νA“äΒΫΏ@àωëπ(zh®Λn)†éΒΡΈ¥¹μΓΘΏ@àωëπ(zh®Λn)“έ÷–��Θ§ΚήΕύ»ΥΆΕ»κΝΥëπ(zh®Λn)ΕΖΘ§Υϊ²É‘ΎÉA≈η¥σ”ξ÷–―Ί÷χΕΗ«ΆΒΡ…ΫΤ¬ΏMΙΞ���Θ§≤Δ«“Αl(f®Γ)≥ωΝΥνêΥΤΨd―ρΒΡΫ–¬ï�����ΓΘ±MΙήΏ@¥Έ±χΉÉΚήΩλ±ΜΤΫœΔΝΥ�Θ§ΒΪ «Ζ®΅χήäΎ÷°ΚσΒΡΥυ”–ΏMΙΞ÷–éΉΚθ‘Ό“≤¦]”–≥ω§FΏ^νêΥΤΒΡΟΑκU––ûι�ΓΘ10‘¬�����Θ§“β¥σάϊΒΡήäΎΑΔ†•±ΑΥΙ…ΫΟ}ΒΡΩ®Τ’άϊΆ–±Μ™τùΔ����ΓΘ”Δ΅χ‘ΎΈςΨÄ―ΗΟΆΆΤΏMΘ§èΡ¥ΚΧλ‘ΎΑΔά≠ΥΙΒΫ«οΧλ‘Ύ≈ΝΥΙ…–†•����Θ§ΕΦΗΕ≥ωΝΥΨό¥σΒΡ¥ζÉrΘ§ΒΪ « ’“φΈΔΚθΤδΈΔ��Θ§Ώ@“≤Φ”³ΓΝΥ’ΰ÷ΈΦ“ΚΆ¨Δήä²ÉΒΡΡΠ≤Ν���ΓΘ
ΓΓΓΓ÷Μ”–•|ΨÄëπ(zh®Λn)àωΥΤΚθΏÄΉ¨»ΥΩ¥ΒΫΝΥ“ΜϋcœΘΆϊ�����Θ§Ώ@¹μ‘¥”ΎäWΥΙ¬ϋΒέ΅χΒΡ ßάϊ�����Θ§”Δ΅χήäξ†’ΦνIΝΥΑΆά’ΥΙΧΙΚΆΟάΥς≤ΜΏ_ΟΉ¹ÜΒΊÖ^(q®±)����Θ§ΒΪ «Ώ@≤ΜΡήΒ÷œϊ1917ΡξöW÷ό•|≤Ωëπ(zh®Λn)ΨÄΒΡ ßάϊΓΘ2‘¬����Θ§…≥Μ Εμ΅χœΤΤπΝΥΖ¥ëπ(zh®Λn)ΒΡΩώüαΘ§‘Ύ ΉΕΦ±ΥΒΟ±Λ����Θ§ÉHÉH‘ΎÉ…²Ä–«ΤΎΒΡïrιgάοΘ§“ρûι ≥ΤΖÜ•ν}±§Αl(f®Γ)ΒΡρ}¹yΚΆ±χΉÉΨΆΆΤΖ≠ΝΥ…≥Μ ΒΡΫy(t®·ng)÷Έ��ΓΘΫy(t®·ng)÷ΈΕμ΅χ300ΕύΡξΒΡΝ_¬ϋ÷ZΖρΆθ≥·ΚήΩλ±ΜΥΆΏMΝΥöv ΖΒΡά§ΜχΕ―����ΓΘ±MΙή–¬’ΰΗ°‘Ύ’ϊ²ÄœΡΧλ»‘»ΜÖΔ≈c“Μëπ(zh®Λn)��Θ§ΒΪ «10‘¬Ζί≤Φ†• ≤ΨSΩΥ»ΓΒΟôύΝΠ÷°Κσ����Θ§•|ΨÄΚήΩλΏM»κΝΥΆ��ΘΜπ†νëB(t®Λi)���ΓΘ‘Ύ“Μëπ(zh®Λn)ΒΡëπ(zh®Λn)†éΏM≥Χ÷–��Θ§Β¬΅χ Ή¥ΈΡήâρ»Ϊ–Ρ»Ϊ“βΒΊΏMΙΞΈςΨÄΝΥ����ΓΘ
ΓΓΓΓ1918Ρξ «ëπ(zh®Λn)†éΒΡΉνΚσκAΕΈ����Θ§ëπ(zh®Λn)†é‘ΌΕ»ΏM»κΝΥ“Μ²Ä“ΉΉÉΤΎ����Θ§Ώ@ΚΆ1914ΡξΒΡ«ι¦rνêΥΤΘ§ΟΩ“ΜΖΫΕΦ¨Λ«σ¦QΕ®–‘ΒΡΆΜΤΤ����ΓΘτîΒ«ΒάΖρ¨ΔήäΚΆΥϊΒΡΒ¬΅χΉνΗΏΫy(t®·ng)é¦≤Ω‘χΫ¦‘Ύ1917ΡξΑl(f®Γ)ΤπΏ^ù™Άßëπ(zh®Λn)����Θ§§F‘Ύ ¬¨ç…œΥϊ“―Ϋ¦≥…ûιΒ¬΅χήä ¬…œΒΡΣö≤Ο’Ώ���Θ§‘Ό¥Έ¦QΕ®ΌÄ“ΜΑ―����Θ§ΥϊΑl(f®Γ)³”ΝΥ“ΜœΒΝ–ΒΡΏMΙΞ––³”�Θ§‘΅àD‘Ύ–¬ΒΫ¹μΒΡΟά΅χήäξ†’J’φΒΊ≤Ω πΚΟ÷°«ΑΆΜΤΤΈςΖΫëπ(zh®Λn)ΨÄΓΘ1918Ρξ3‘¬�����Θ§τîΒ«ΒάΖρΑl(f®Γ)³”ΝΥΙΞ™τ––³”�����Θ§Ώ@¥Έ––³”éΉΚθΑ―”Δ΅χήäξ†≈cΖ®΅χήäξ†ΥΚΝ―ΝΥ�����Θ§κSΚσΒΡΈΘôCΤΫœΔΝΥΝTΙΛΦΑΥυ”–ΒΡΖ¥ëπ(zh®Λn)―‘’™����ΓΘΒΪ «Ή‘èΡΑl(f®Γ)³”ΝΥ1916Ρξ“‘¹μΒΡ Ή¥ΈΙΞ™τ�Θ§τîΒ«ΒάΖρ“≤Β»”ΎΑ―¥σΝΩΒΡΒ¬΅χήä©¬Ε‘ΎΝΥÖf(xi®Π)Φs΅χΒΡΜπΝΠ÷°œ¬�����ΓΘΒ¬΅χ“ΜΙ≤Αl(f®Γ)³”ΝΥΈε¥ΈΏMΙΞ�����Θ§ΤδΙΞ³ί“Μ¥Έ±»“Μ¥Έ»θ�Θ§Ώ@ «“ρûι Ω±χΒΡ²ϊΆωΚΆι_–Γ≤νΒΡ§Fœσ‘λ≥…ΒΡΓΘΒΫΏ@²ÄïrΚρ��Θ§Öf(xi®Π)Φs΅χΒΡΖβφiι_ ΦΑl(f®Γ)™]Ής”ΟΝΥ��Θ§ΑΊΝ÷»ΥΖ≠±ιά§ΜχΕ―¨Λ“£Η·†ÄΒΡ»βνêΚΆ Ώ≤Υ”Ο“‘≥δπ΅�Θ§Υϊ²É“Σά^άm(x®¥)³Ύ³”ΒΡ‘£ΟΩΧλ÷Ν…Ό–η“Σ1000Ω®¬ΖάοΒΡΡήΝΩΘ§Ώ@Ώh±»ΙΌΖΫΒΡΉνΒΆœόν~ΒΡ“ΜΑκΏÄ“Σ…Ό�ΓΘ1918ΡξœΡΧλ���Θ§”Δ΅χΚΆΖ®΅χΒΡήäξ†ΒΟΒΫΝΥΑΌ»fΟάήäΒΡ÷ß≥÷��Θ§ι_ Φœρ«ΑΆΤΏM�����ΓΘ°îïrΒ¬΅χΒΡ™ζ–Ρ «�����Θ§»γΙϊëπ(zh®Λn)†é≥÷άm(x®¥)ΒΫ1919Ρξ���Θ§Οά΅χ¨ΔΑl(f®Γ)³”“Μàω¦QΕ®–‘ΒΡΏMΙΞ�����ΓΘΏ@ΖN‘Oœκ™τùΔΝΥΒ¬ήäΒΡ Ωöβ�����ΓΘΒΪ «‘Ύ1918Ρξ�����Θ§Ώ@–©Ρξίp»Υ»‘»Μ‘Ύ”H…μσwïΰëπ(zh®Λn)†éΒΡ±ΨΌ|���Θ§≤ΔûιΏ@ΖNΧ™èà¬ï³ίΒΡ³ΌάϊΗΕ≥ωΝΥΨό¥σΒΡ¥ζÉrΓΘ1918Ρξ«οΧλ��Θ§”Δ΅χήäξ†ι_ Φ»ΓΒΟΉνΫKΒΡ³ΌάϊΓΘΚΎΗώΡ«ïr÷Η™]÷χ60²ÄéüΒΡ±χΝΠ�Θ§Ώ@“≤ «”ΔΒέ΅χ÷Η™]Ώ^ΒΡΉνèä¥σΒΡήä ¬ΝΠΝΩΓΘΥϊ“‘≤Ϋ±χ��ΓΔΧΙΩΥ�����ΓΔοwôCΚΆ≈Ύ±χ¬™ΚœΉςëπ(zh®Λn)ΒΡΖΫ ΫΆΜΤΤî≥»ΥΒΡΖάΨÄ≤Δ“‘¥Υ»ΓΒΟΝΥ³Όάϊ���Θ§Ώ@Άξ»Ϊ≤ΜΆ§”Ύ1916ΡξΒΡëπ(zh®Λn)–g���ΓΘΉνΫϋ”Δ΅χöv Ζ¨WΦ“à‘≥÷’JûιΚΎΗώΒΡ³Όάϊ≥÷άm(x®¥)ΝΥΓΑΑΌΧλ÷°ΨΟΓ±Θ§Εχ«“Υϊ²É“≤’JûιΏ@ «ΥςΡΖΚ”ëπ(zh®Λn)“έ“‘¹μΒΡ≤Μîύ¨WΝïΏ^≥Χ÷–ΒΡ“Μ²ÄΗΏ≥±��ΓΘ15
ΓΓΓΓ‘ΎΝς―Σ÷–ΒΟ¹μΒΡΏ@–©ΫΧ”• «Ζώ÷ΒΒΟ����Θ§»‘»Μ «“Μ²Ä“ΐ»Υ†éΉhΒΡÜ•ν}Θ§ΒΪ «ëπ(zh®Λn)†éΒΡΉνΚσκAΕΈ¥_¨çΫ“ι_ΝΥ±ΨïχΒΡ–ρΡΜ��ΓΘ1918Ρξ11‘¬ΒΡëπ(zh®Λn)†éΚσΙϊ��Θ§Ϋ^¨Π≤ΜÉHÉH «σw§F‘ΎÖf(xi®Π)Φs΅χΒΡήä ¬³ΌάϊΚΆΆ§ΟΥ΅χΒΡ ßîΓ����Θ§Ώ@àω»ΪΟφëπ(zh®Λn)†é ßîΓΒΡ¥ζÉréß¹μΒΡ «÷»–ρΒΡ»ΪΟφ±άùΔΓΘ°îτîΒ«ΒάΖρœρÖf(xi®Π)Φs΅χ“Σ«σΚû πΆΘëπ(zh®Λn)Öf(xi®Π)ΉhΒΡïrΚρ�����Θ§Β¬΅χΟώ±ä¥σûι’πσ@����Θ§τîΒ«ΒάΖρΫo≥ωΒΡάμ”… «Β¬΅χ“―Ϋ¦Οφ≈R΅ά÷ΊΒΡάßΨ≥Θ§ëπ(zh®Λn)†éüoΖ®ά^άm(x®¥)¥ρœ¬»ΞΝΥ����Θ§ΨoΫ”÷χΒ¬΅χΒΡΚΘήäΑl(f®Γ)³”ΝΥ±χΉÉΘ§Β¬“β÷ΨΒέ΅χ‘ΎΥΡ²Ä–«ΤΎΒΡïrιgάοΨΆ±άùΔΝΥ�Θ§ΨΆœώ“Μ²ÄΦàΚΐΒΡΖΩΉ”“Μ‰”≤ΜΩΑ“Μ™τΓΘΒ¬΅χΜ Βέ±ΜΤ»ΆΥΈΜΝΥ���Θ§κSΦ¥ΥϊΝςΆωΒΫΝΥΚ…Χm�����Θ§ΥϊΒΡΦ“Ήε‘ΎΒ¬΅χΑΊΝ÷ιLΏ_500ΕύΡξΒΡΫy(t®·ng)÷ΈΨΆ¥ΥΫKΫY�ΓΘΙΰ≤ΦΥΙ±ΛΆθ≥·Ϋy(t®·ng)÷Έœ¬ΒΡäW–ΌΒέ΅χ“≤ΫβσwΝΥ��ΓΘ11‘¬8»’Θ§°îïrΡξÉH31öqΒΡΩ®†•Μ ΒέΉνΚσ“Μ¥Έ’Ψ‘ΎΨS“≤Φ{Οά»Σ¨mΒΡΈηèdάοΟφ��Θ§Ώ@²ÄΩ…ëzΒΡΡξίp»Υ ß»ΞΝΥ§îϊê΄I·ΧΊάΌ…·ΒΡ»AϊêΙβ≠h(hu®Δn)����ΓΘ’ΐ»γ“Μ²Ä’ΰ÷ΈΦ“”^≤λΒΫΒΡΡ«‰”Θ§Ώ@‰”ΒΡ“Μ²ÄàωΨΑ «Οϊ¬ï≈côύΝΠΒΡΉν¥σ±·³Γ–‘œσ’ς���ΓΘ
ΓΓΓΓ°î»Μ��Θ§³ΌάϊΒΡ¥ζÉr °Ζ÷ΗΏΑΚ���Θ§Öf(xi®Π)Φs΅χΚήΩλΑl(f®Γ)§FΥϋ²ÉΚήκyΏmëΣΏ@‰”ΒΫ¹μΒΡ“Μ²Äëπ(zh®Λn)Κσ άΫγΓΘ»γΙϊ’ΐ»γΧmΥΙΕύΕς³ΉΨτΫ®ΉhΒΡΡ«‰”�Θ§ëπ(zh®Λn)†é‘Ύ1916ΡξΫY χΒΡ‘£Θ§ «ΖώïΰΫΒΒΆΏ@àωëπ(zh®Λn)†éΒΡûΡκy–‘”ΑμëΡΊ���ΘΩ»ΜΕχëπ(zh®Λn)†éΒΡά^άm(x®¥)Φ»¨ΠΫΜëπ(zh®Λn)κpΖΫ‘λ≥…ΝΥΤΤâΡ–‘ΒΡ¥ρ™τ��Θ§“≤¥ίößΝΥöW÷όΒΡ≈f÷»–ρ����ΓΘ
ΓΓΓΓ“Μëπ(zh®Λn)ΒΡΉνΚσκAΕΈ «Ζ«≥����ΘΜλ¹yΒΡΘ§Υϋ“≤ «±ΨïχΫ”œ¬¹μ’¬Ιù(ji®Π)ΒΡ“Μ²ÄΜυ±Ψ±≥ΨΑ�����ΓΘκS÷χΙΰ≤ΦΥΙ±ΛΆθ≥·���ΓΔΝ_¬ϋ÷ZΖρΆθ≥·ΚΆΜτΚύΥς²êΆθ≥·Ϋy(t®·ng)÷Έœ¬ΒΡ÷TΒέ΅χΒΡΦäΦä±άùΔ��Θ§Υϋ²ÉιLΤΎΫy(t®·ng)÷ΈΒΡ÷–öWΚΆ•|öWΒΊÖ^(q®±)≥ω§FΝΥôύΝΠ’φΩ’�����Θ§’l¨Δ‘ΎΏ@άοΑl(f®Γ)™]–¬ΒΡΧφ¥ζ–‘ΒΡΉς”ΟΡΊ�ΘΩ≤Φ†• ≤ΨSΩΥΒΡΗοΟϋéß¹μΝΥ ≤Ο¥‰”ΒΡΧτëπ(zh®Λn)���ΘΩ‘Ύ“Μ²ÄΆΕΤ±ΒΡΟώ±äΨυ±Μ”•Ψö≥…ûιöΔ ÷ΒΡ΅χΦ“άο�����Θ§¥σ±äΟώ÷ςΡήâρ≥δΖ÷ΒΊ¨ç§FÜα����ΘΩ“Μëπ(zh®Λn)÷–Θ§÷≥ΟώΒΊΒΡ»ΥΟώ“―Ϋ¦Ϋ” ήΝΥΟώΉε÷ςΝxΚΆΟώ÷ςάΥ≥±ΒΡœ¥ΕY��Θ§‘ΎΏ@ΖN±≥ΨΑœ¬���Θ§÷≥ΟώΒέ΅χ»γΚΈ”––ßΒΊ÷ΈάμΥϋ²ÉΒΡ÷≥ΟώΒΊΚΆ³ίΝΠΖΕ΅ζΡΊ�ΘΩÖf(xi®Π)Φs΅χ»γΚΈ÷ΊΫ®“Μ²Ä“―Ϋ¦±Μ¥ίößΒΡ»Ϊ«ρΌY±Ψ÷ςΝxσwœΒΡΊ�ΘΩΫ¦övΏ^ΥΡΡξΒΡëπ(zh®Λn)†éΆάöΔ÷°ΚσΘ§’lΗ“Άΐ―‘»ΥνêΈΡΟςΒΡÉr÷Β��ΘΩΕχ«“��Θ§Ήνûι÷Ί“ΣΒΡ «�����Θ§1919Ρξ‘ΎΑΆάηΨÜΫYΒΡΚΆΤΫÖf(xi®Π)Ε®ΡήâρΨS≥÷œ¬»ΞÜα?Ώ@–©Ü•ν}‰΄≥…ΝΥ±Ψïχ«ΑΑκ≤ΩΖ÷ΒΡ÷ς–ΐ¬…��Θ§“≤ ΙΈ“²ÉΡήâρèΡ“Μ²ÄΗϋΦ”΅χκHΜ·ΒΡ“ïΫ«¹μΤ Έω”Δ΅χ¨Π”Ύ1918ΡξΏ@ΕΈöv ΖΒΡΖ¥ëΣ����Γ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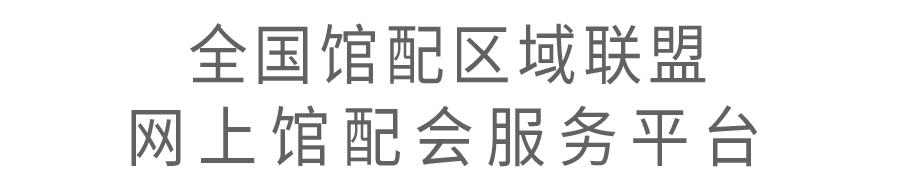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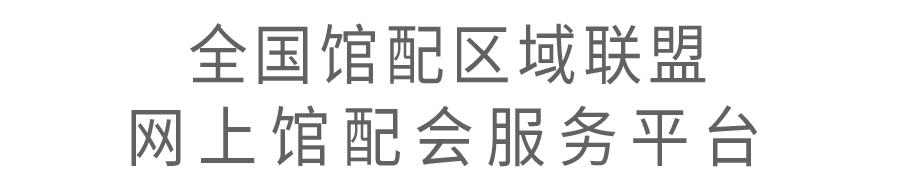


 ïχÜΈΆΤΥ]
ïχÜΈΆΤΥ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