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娜爾的散文猶如哈薩克族草原歌曲一般悠長動人����,飄散著青草和云朵之香。
劉亮程
阿娜爾寫了親情��、家族�、美食、庭院內(nèi)外等等��,她從伊犂出發(fā)���,走得或遠(yuǎn)或近����,但身上一直背著族別和家世。這是少數(shù)民族作家共有的特點(diǎn)�����,尤其是用漢語寫作表達(dá)后�����,其辨識度極高����,亦顯得極為獨(dú)特和生動。
王族
心靈記述者阿娜爾
(代序)
第一次見阿娜爾的時(shí)候����,她很熱情地用流利的國家通用語對我說,王老師����,我想讀您的研究生,不知是否有機(jī)會�?我問她,你為什么想讀研究生呢��?她說���,希望能學(xué)習(xí)到更多表達(dá)心靈和記憶的表述����,說的時(shí)候��,笑出潔白的牙齒��,陽光下閃閃發(fā)亮���。我說�,你更適合從生活中尋找書寫心靈��、吟詠性情的文字����,并勉勵(lì)她好好寫作,不承想�,兩年不到的光景,她便陸續(xù)寫出了一部散文集�����,洋洋灑灑二十幾萬字����,名為《走過六百公里》�����,我想����,這里的走一語雙關(guān)��,不只是旅途行走�,更是一種緊貼家鄉(xiāng)記憶的心靈行走。借助散文重溫舊事���,不免發(fā)現(xiàn)�,生命的書冊里最美好的�,仍然是其中某些段落帶來的回憶,所有對心靈的記述大抵都會回到童年�、回到家鄉(xiāng)、回到初心�。她與我閑談時(shí),談家鄉(xiāng)�����、家庭、工作與寫作愛好之間的平衡也頗多�,偶有煩擾����,但每談及寫作、女兒和伊犁����,她的表情便格外明亮起來。
在她筆下����,家鄉(xiāng)諸事均是心靈詠嘆之對象,個(gè)人經(jīng)歷與地域游歷以及生活中的五味雜陳相混合�����,一個(gè)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她的敘述主體通過散文這種文類得以形塑����。她會說:伊犁第一的美譽(yù)是有時(shí)間重量的(《走過六百公里》);她也會說:打破長久的沉默�����,也或者幫他找一個(gè)撕開陌生走向熟悉的突破口(《在大巴扎逛街》)。
她的直覺銳利��,體現(xiàn)在文字中�,更多表現(xiàn)為通過色彩修辭所表達(dá)出的一種情緒感知,它們?nèi)绱缩r活��,帶有對新疆南北疆幅員遼闊地域感知的詩性思維活躍其中����。她會用紫色形容一時(shí)年少的激情(《薰衣草和我》);用藍(lán)色形容一種情感的偏好(《藍(lán)色浪漫》)�����;用白色形容一種對季節(jié)更迭的心境(《我在烏魯木齊》)����;用紅色和黃色描寫一份精神性的雀躍(《在大巴扎逛街》);用金色去形容主體所遭遇的炫目感(《一
棵樹》)���。
難得的是��,在她的散文中��,比擬并不止步于形象間的一種簡單的相似關(guān)聯(lián)���,而是具有一定深入思考的程式�����,與象征性相通,難免又蘊(yùn)含一些類似小品文的哲思����。比如她散文的第一輯中,會將烏魯木齊與一棵榆樹的姿態(tài)關(guān)聯(lián)���,認(rèn)為它時(shí)而孤傲�����,卻又自給自足��,頗像是對自己早期在烏魯木齊漂泊的一種境遇自況�����,但它有時(shí)又像一把庇護(hù)傘�,白色外衣下有股力量在燃燒像在替所有膽戰(zhàn)心驚的人守護(hù)平安��,這又像是對思念自己良師摯友的一種移情了。
總之��,看她的文字和看她的人�����,感到樂觀�、積極和充滿朝氣,像春夏之季伊犁河谷平原生長出的一株植物����,那么生機(jī)勃勃。當(dāng)然�����,也并不是要借助序言���,總說一些溢美之詞���,文中也有許多瑕疵。作為她的第一部散文集�����,零星收錄的均是她自2014年開始陸續(xù)發(fā)表在《西部》《新疆日報(bào)·副刊》和《烏魯木齊晚報(bào)·副刊》上的文章,還很不成體系���,缺乏一個(gè)一以貫之��、形散神聚�����、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題;在散文格調(diào)的運(yùn)思上����,她也欠缺一份過盡千帆皆不是的閱歷,少了些直指人心的鋒芒�。此外,語言的錘煉上她的確還需更加努力�����,若能刪繁就簡�����,左右推敲,巧設(shè)機(jī)關(guān)�,令人渾然忘我,仿佛置身更加富于生氣的文學(xué)氛圍中���,怕就更好了�����。
然而�,瑕不掩瑜�����,在我所接觸的為數(shù)不多的哈薩克族青年女性作家中�,阿娜爾的散文里有一種難得的理性和思辨力量。不是每個(gè)人都能偷得浮生半日閑般�,有把生活記述成散文的余暇;也不是每個(gè)人都具有將瑣碎日常升華為哲理小品文的余韻��,擁有這份余暇和余韻�,是阿娜爾的運(yùn)氣和福氣。
這份運(yùn)氣和福氣在一位心靈記述者寫作的初期�,總能扮演一個(gè)有價(jià)值的角色。這本文集就是最好的證明����。希望不久的將來����,也能成為她的底氣���。
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烏魯木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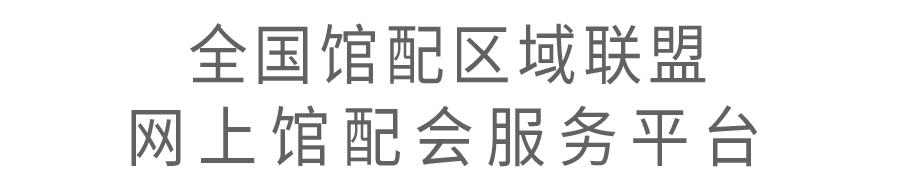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